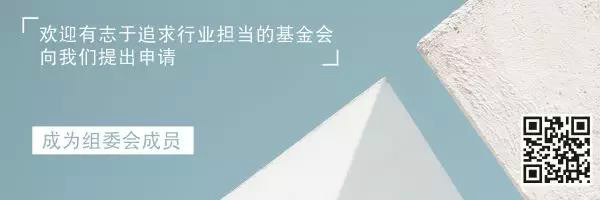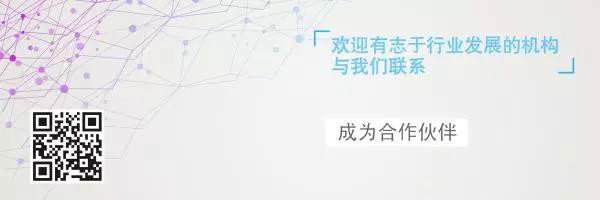在5月6日推送的“探讨互联网慈善背后的真假问题:科技向善吗?”一文中,作者从事实运用和细节说理两个角度对“技术神话”一文进行了重新梳理,引出了这4个问题:1)“同情”或“认同”:“同情疲劳”是现代慈善的最大危机吗?2)“不对等”问题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应如何看待?3)如何看待“平台”的商业利益和议程设置问题?4)“技术是中立的吗?”抑或我们应换一个问法。将技术对公益慈善的影响剖析得更为深刻。
本文,我们沿着这4个问题,继续推送作者对这一话题的现实思考。

photo by timJ, on unsplash
反思慈善对“同情”的过度消费:借助技术助力,倡导理性慈善
笔者认同原文指出的“同情”被过度消费的问题,但与原文不同,笔者以为,倡导理性慈善正是可行的应对策略,而技术则可以被作为支持手段来使用。对于原文所反对的“捐助者监督”,笔者恰恰认为,借助技术手段来支持捐助者监督,恰是发展理性慈善的有效手段。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理性慈善”能够带来的增值效应:
“因感动捐出一份爱心,助力公益的份额之一;
关注爱心实现的过程,通过关注,对公益形成监督,有助于提升公益责信,助力公益的份额之二;
因关注,了解公益项目的优劣好坏,有选择地对那些好项目追加捐赠,不仅有助于公益市场选择机制的发展,也更将爱心资源用于合适之处,助力公益的份额又何止其三。
同样一份爱心,理性捐赠人在献出同时还附上理性与责任意识,则由这一份爱心实际带来的社会效应,产生不止三倍五倍的增长。”
(参看:平台兴起 互联网公益几点观察)。而“理性慈善”,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才更能很好地发展。
公益慈善平台体系可进一步完善 志愿服务平台是新的成长点
笔者通过反驳原文“去行动化”这一观察概括,提出了互联网平台技术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应用不限于捐赠的观点。除了起步较早、相对更为成熟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之外,志愿服务平台同样正在兴起。可以想见,在志愿服务领域,我们同样可以期待平台技术的多重作用:服务记录、供需匹配、参与激励等等。当然,志愿服务平台的发展,仍需克服数据记录的核实、标准化等种种难题,但此类平台在今后更完备的公益慈善领域平台体系中将有不可或缺的位置。
公益慈善平台应加强可持续发展机制建设
原文讨论了平台的“商业利益”问题。笔者虽不同意原文的观点,但受其启发,认识到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值得关注。平台可在“慈善新体制”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主管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中间层次,一举改变原有的社会管理格局,向治理、共治模式过渡。但平台本身的运转,也需要成本来维系。如不能建立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平台的发展将是不稳固的,向“新体制”过渡,也可能遇到阻碍。
因此,收益用于平台自身发展的营利模式探索应当肯定,关键是要在平台营利与公益慈善资源之间建立起严密隔离,使其相互间无法混同、干扰。如果平台营利能力不足,也可探索多种成本来源共同支撑的模式,以社会捐赠、政府购买服务、平台自身营利并行的方式提供支持,保证平台的可持续运转。

photo by Marcos Luiz Photograph, on unsplash
公益慈善平台应加强议程设置、规则供给方面的研究与公众参与
平台本身由企业或社会组织主体来运营,但同时又作为中介组织为供需双方提供服务。公益慈善领域中的平台,既提供服务,又供给规则;既规制行为,又参与治理。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平台具有企业与市场的“二重性”(陈永伟,2018)。把视线拉回公益慈善领域,其中的平台同样存在“二重性”:总是负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社会治理机制的建设、供给、维护者,另一方面也身处市场、社会当中,有自身利益,受相关机制的约束。单方面否定其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身份或否定其自身利益,都是不切实际的。正是由于平台的议程设置、规则设计与维护不仅关乎其自身,还关涉众多相关方的权益,有着明显的公共性,因此更值得研究:什么样的规则才是更公平、更合理的。
除规则的实质内容值得关注之外,规则的制定程序同样值得关注:由于平台不仅是服务提供方,还是规则制定者,所制定的规则又涉及平台之外各类主体的权益,因此从程序正当性的角度,平台规则的制定、议程的设置应注重“公共参与”、吸收外部意见与建议。在这方面,腾讯公益邀请相关方共商“99公益日规则”的做法颇值得肯定。
以上四点,即为笔者阅读原文、进行观点对话之后的主要思考。其实原文所点到的、值得讨论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四点。例如,原文指出的:慈善资源的过度集中、公益项目赢者通吃、慈善生态圈层化等现象,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人所共睹,值得认真对待。此外,原文涉及到的“技术”、“数据”、“科学”等在公益慈善领域的话语垄断问题,同样也值得研究者、从业者深思。这些话题的归纳、呈现,正体现了原文价值。此等处笔者的研究不到,也就无法着墨了,并非原文未涉及。
延伸思考
以上的讨论也算比较充分,原可就此搁笔。但笔者在撰写此文时,不禁思考,为何笔者能够认同原文作者的问题意识、问题提炼,但对问题的思考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带着这一问题,笔者又重新阅读了原文正文及注解。在注解中,作者花了较大的篇幅,引用、解释了“公益”与“慈善”的差异;在正文结尾处,作者又提出了“社会主义语境下的慈善事业”的说法。由此,笔者不免对作者的思路有了较模糊的印象,并产生了一些联想。未必合适,同样也分享如下。
首先是关于“公益”与“慈善”的区别问题及其研究思路、意义的联想。
“‘公益’与‘慈善’有无区别?区别何在?”
这一问题当然有其价值,并且不仅有理论意义,更有现实意义。研究方法,当然也可以有语义分析的方法、词汇史梳理、语种间比较等多种方法。但笔者总想,不管以何种方法研究,最好能观照现实,在最根基处的学术与最直接的实践之间建立直接的对话。笔者以为,带着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上述问题不仅是语义澄清问题,更是语用变迁问题,是社会建构问题;例如,慈善领域立法为何舍“公益”而以“慈善”作为核心概念,又将带来何种影响,恰是社会现象、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而并不能给前述问题提供充分的答案。
其次是对固有观念的反思。
当此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点,我们仍需澄清概念、正本清源。
进入公益慈善领域的讨论,既要抵御片面强调公益“市场化”、“规模化”等话语的侵蚀,也应正视此类口号的合理性;对“商业”、“市场”、“公有”、“私有”等概念做更彻底的反思。“市场”有无原罪?“商业”有无原罪?所有权呢?“公”与“私”这一组概念之中,是否一个比另一个在道德上天然优越?“营利”与“非营利”呢?“国营”与“民营”呢?如果不对一些固有观念加以反思澄清,而仅出于对“公平”的追求、求“平等”的善意,往往容易行差步错、似是而非。
让我们返其根本、再出发——以此与诸君共勉。
本文作者
汪伟楠

汪伟楠,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非营利组织管理方向。
注:本文为投稿作品
谨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编辑 | 洪峰
网站编辑 | 江吉瑶
基金会论坛最新好文